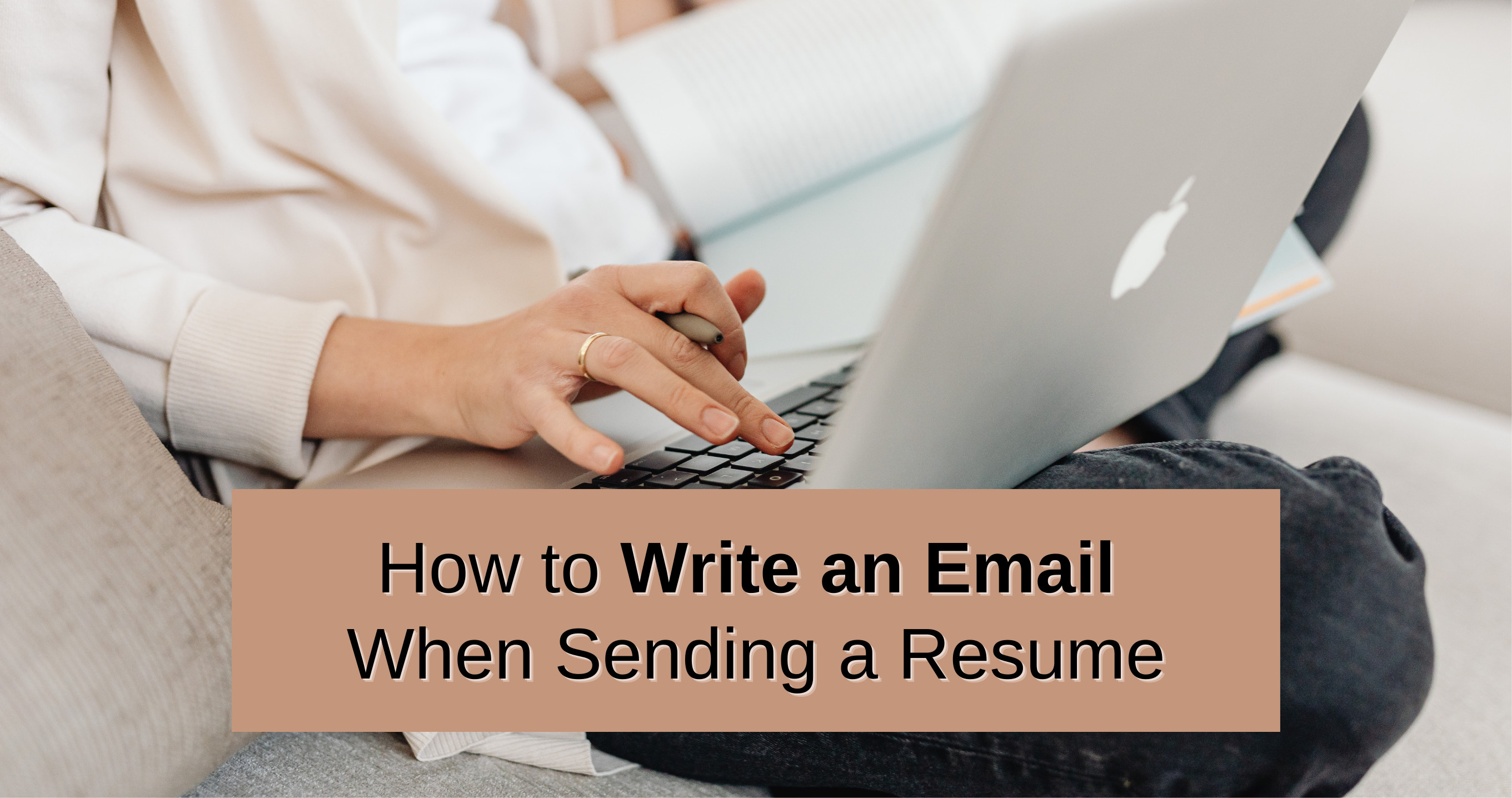夜半計程,車與大衛.鮑伊 (Space Oddity)
夜晚在歌唱與歡愉之後
饗宴,我們攔車離去
同一位男子招呼一位司機先生
車內的音響傳出新聞畫面卡住
社會問題的聲音,或者無關生活的八卦
像在耳中播送的大衛·鮑伊
我想是他正在說些重要的事情
嚴謹阻隔我與周圍菸般凝滯的空氣
黎明之前的車陣安寧而繚亂
我的祖先督促我趕緊離開黑暗
與大衛說著聊著祂們知道的事
以我知曉而未識的語言交談
我只能簡單的說你好、謝謝
喚我僅有的族裔
枝聲朽幹
帶著夜中工廠的聲音輕訴
伐伐那漂流木,點點細語
在車中,無所謂流動而馬路好寬
像要渡過海洋
夢在遠處支流
又重聚里程
迷航
時以一些生活關係計算
在路上
身而為原住民我很抱歉——讀乜寇〈我在我自己的土地上被逮捕〉有感
在總統道歉之後
新聞上那一個我
像個犯錯的孩子被抓到了
因為回到森林
學祖先的生活方式
獵槍不須要被折斷
但人要被關起來
槍留給下一個人用
是為了傳承
不是為了也可能被抓
開山的刀不須折斷
但人被關起來
刀留給下一個人用
是為了尊嚴與文化
不是為了讓下一個人也可能想殺
他們以為我們就是這樣
只有草莽
不住這裡的人
傳承我們文化的方式
是告訴年輕人
我們會砍別人的頭
他們不懂生活
不懂這裡的生活
當他們知道時,還是這麼做
吳鳳不很無縫
鄭成功不成功
掠奪的人
全社會幫助他們成為傳說
石頭讓人採去
木頭讓人砍去
山在哭,我看著祂一直被砍頭
懂得生活的人通通關起來
讓他人的法定讞我們有罪
在牢裡叫喊:
「稱為原住民以前
我們都還有自己」
都還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與決定如何生活的方式
然後再也不會有人學會使用開山刀、獵槍
因為他們所謂的文化人
就是用法律、怪手
和一堆錢
換來的玩具傀儡
我說祖先,我沒有錯
但身為原住民
了斷一切噩事的道歉方法
我問?
能不能學總統
(記2015年王光祿獵槍案)
逐漸混色的海洋──致夏曼‧藍波安
我與睡著的防風樹說起族語
它不懂語言隔閡的嘆息
像是蘭嶼之於台灣母親
臍帶,像山蜿蜒
入海的羊水
被浪花層層剪斷
從此失去接連的血液
海溝的深度如腦皺褶
潮潮摺來的波狀
以為頰上的紋也漲潮了
詩聲的舞姿
與太陽正漸漸漏氣
祖靈的眼睛留在岸上
成為過時的魚皮
和漂流木
離枝落葉潛入水中
沉澱,很黑很黑的視線
黑到我以為不是黑夜
只是雙眼被海風宿醉
老海人唱的詩歌裝進酒瓶
酒精射不準魚
而我的舌射中酒精
在大海中漂浮的夢
都是酒鬼的影子
都只是一群被孤獨慰藉的飛魚
又在夜晚與睡著的防風樹
說話,聽它的夢囈
聽見葉子終於嘆息
期待是不是也曬乾了小米
酒醉的拼板舟
射魚時,蒐集著閃閃發光的鱗片
漂著浪裏忘記疼痛的血
汛期,看見海上跳躍的月
讓海的顏色越來越深
深深的藍,深深的夢
深深舟腹,深深是家
製成飛魚乾癟的求生
意志和我
眼底的靈魂踏浪時依舊浮動
白日靠岸,不該坦露剝開海的顏色
剩下多少綹祖靈的聲線在拉著我們
達岸附石而乾的鹽巴
都沒吃過幾次
和飛魚一樣
因為更能獵舌的食物,忘了
提早回家
(2016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佳作)
初次嘗試原住民族文學創作投稿至文學獎,粗淺的從文學創作、社會觀察的角度去探問蘭嶼現代化過程及原住民族混血身分者的認同焦慮。
不在之地
總是要抄襲昨日走過的路
在晨霧中重複呼喚陌生的家
半路找尋不存在的分身
問我時間,為何總是放棄原來名諱?
為何村口違和的水泥拱門名為上田組部落?
Sadida'an的母親說:「dida是太陽出來了的地方
Cidal的腳被dida給粘住
光明複沓在土地上
Sadida哪裡的泥巴會粘在我腳上
那裡就是我的家。」
Cidal越過海岸山脈的背
從老家背後的小耳朵聽見:
「Sadida'an位於長濱海階上方,
北倚都巒山層,由西向東傾斜。」
──資訊網的電子音如是說。
這裡水田一一廣布
還不到那一句水田不要賣
或許將之視為喚醒的方式
或當一個能被喚醒的人
一種還愛聊天的文字
dida上的老人家點播089
用部落的嘴巴告訴我
幾句陌生日文的借詞族語摻雜台語
用我學不會的那一種什麼都會種的聲音
96.3對於政治議題總是消化出不良反映
海是要多聽一切上帝的福音
還有農會來的年輕人發敬老金
狩獵部落的工作夥伴
有些時候紅包比三合一(的我)好溝通
在抵達靈魂歸所之前
即使文健站的預算跌倒還是要多編織一點躺下費
月亮七點
精神的播種祭
隔壁家族過年宗親會歡欣熱舞
座前的父女淺淺對話:
為什麼我們沒有唱族語歌?
「不行。
我們只能唱
教會的詩歌。」
西部來的我思考著
那是否還能視為文化的另一種傳統?
走在村落三叉口休止找尋的腳步
牆的時間斑駁延伸至十架教堂
彷彿規馴著正凝視我的神
金剛山下田野青綠
那我不被種植在此之地
阿美族語註釋:
Sadida'an,很多泥巴的地方,行政區:上田組。
dida,粘土。
sadida,粘土會粘在腳上之意。
Cidal,太陽。
(2021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佳作)
〈不在之地〉是我近幾年返鄉的經驗汲取出的一滴反饋。
試論我母親的故鄉──長濱Sadida’an遭遇的宗教殖民與鄉村政治現代化過程,各種勢力交錯之下的生活景況,我不斷思考所發現的尷尬,它們像不義遺址一樣建立在實景之上,在村人進入部落時會有一座拱門上寫著「上田組部落」,那曾是讓我疑惑的五個字,在認識自族文化時,我必然也明白了長濱海階上的下田組、田組、上田組,這一層層遞近向山的日治時期規劃的行政區,尚未回復傳統的名字,當地有滿滿的水田與黑土,但你少見小米,也沒有人會在農地工作時一邊唱著〈鋤草歌〉,西部來的我思考著,那些已消失的是否還能視為當地人的文化傳統?
或許鄒族菁英高一生那句:「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水田不要賣。」其實也訴說著其他不應該被換掉、賣掉的傳統文化。
剝裂自己時須先進行的儀式
1.
我須要無盡的新生
傾聽屬於我的山洞,向世界回應
山靈一再剝蝕未癒的竅穴
汩汩流動著,你問源頭漂移的上游
如何尋覓,得以拯救
而你還是不會懂什麼叫作鄉愛
指望你,像後敞褲將雙腳放開
走一條開闊亦孤獨的荒徑
研究你的語言如何發展
告訴你事件的發生是假設的
從刀鞘中滴落的血認定煙硝處襲吹而來的風向
獸徑前往的方向來告訴你
你還有家。
但無法前往,無法探望
2.
都是一家人,故事都是相同起始的覆述
不必特別去尋找曾經,所謂神靈說已經給你
悲傷事跡都有足夠理由使你自由肉體
再一次回答你,你沒有文字,沒有可以
記得的姓名
沒有正確且健康的咀嚼方式
吐出混淌在一團傷殘歷史中榮耀的酒漿
像是僥倖逃入山洞的人
看不見你沒入寂黑的瞳色,失溫的苧麻
一株影子裏亦遭人唾擲
3.
把雙眼給忘記時
深墨色的琉璃珠眼淚
像情人已輕巧落下
溪流的靈魂
在沒有鏡子的年代湧出來
村人相視彼此面龐連成命運
在碎散的杜虹花中
結累幾粒果實,落地
像極地上的星直盯著篝火閃焰
4.
關於完成生活,思鄉是鄉人未識的單詞
各地的神與祖靈啊!已遺忘的美
該如何區別與揭示?
遺忘是遺忘者的山洞
變成木頭的樹不能再長成一棵樹
祈求回答以後
舞,種植新的自己
讓所有剝裂的模樣
去祭祀
5.
祭刀的記憶是消逝的
一條長徑筆直切開
切過山與海,不再耕種的豐饒之地
它善於遺忘苦痛
切開一切
將神話放入刀鞘
如我勉強從擱淺的溪流撈上語言開始
被草木悲情流離的殘酷都市拯救的歌
善於傾聽焰火、傾聽風
前往的方向來告訴你
我將要再次死去
(2021台灣文學獎 原住民華語文創作獎新詩入圍作品)
在我身體裡的那座山
Cecay、歷史
在Siraya與Kebalan還沒走到石坑山
海岸一直往山的東側靠過去親吻太陽的臉
天晴時,西邊的山崖秀出白髮
猩猩露出顏面的深邃
溪流是牠在雨中洗澡流下的水跡
一顆顆單石與石輪鑲嵌在村落矮房與石墻中
遺留古時候殘存的記憶
像Pikacawan面色不改的守候佇立
Kakacawan的人用拔黃藤的力氣
在泥巴地耕造出金色的海洋
暮落來臨
我摸黑尋找年祭消失的原因
古老黑山與紅藜色交錯了命運
十字繡紋跳起歡迎歌舞弄二十一世紀
手中的小米穗結籽成星星
如露珠是洪水後裔
後裔的情人 眼淚汩汩在坡地邊滾動
染紅的雲群隨風飄向大道直達太平洋……
也在我身體裡成為故事
Tosa、行走
耆老輕訴著……
「行走要像太陽,心要像月亮謙卑守護,
兩者並行,才是一位阿美族人。」
我試著當一位採集思想的阿美食家
沉默割除漫佈的荒草
向山靈打招呼
在水田邊做Mipurong
累的時候搓搓肉桂葉抹在額頭
祖靈會叫醒你的腦袋
將檳榔鞘葉折成凹形
山萵苣、羊奶頭、野莧菜,一隻山雞加些許刺蔥
葉底擺滿麥飯石與溪流的汗
酌一杯萬壽菊、黃藤、過山香釀製的酒
太陽很大 突然想和風雨一起Pakelang
Tolo、在路上
風雨猛烈拍打茅草屋的梅雨季
想起仍有寡婦吟唱祈雨歌的旱地
再再想起柏油路覆蓋母土
悲喜紛雜生出我的那時代越來越近
城市像藤叢般強悍的隨地盤生
我想當一台割草機以嘴溫柔狩獵
以舌辨識城市與部落中不同的阱陷
以嗓子發出燻火的熱烈與大山的峻竦
向禽魚鳥獸學習四肢的運用
攀爬書寫秘密與祝福:
「Rayray ko toas a lalan tayra i dao’c.」
是每一種存在中的眾神正在圍舞
在每一座Taparo頂上唱起Radiw
黑暗中一顆顆汗水與呼息凝結成琉璃隱隱墜落
是一支發光的大冠鷲羽毛在構樹上巧落
古老宇宙瞬顫起微緩卻永恆無止的漣漪
那美好夜晚不斷告訴我:「張開嘴,就是路。」
註一:Siraya,西拉雅族。
註二:Kebalan,噶瑪蘭族。
註三:Pikacawan,瞭望臺。
註四:Kakacawan,長濱舊稱「加走灣」。
註四:Mipurong,舊時阿美族人結草佔地所做的標記。
註六:Pakelang,阿美族人婚喪喜慶、勞務之餘,慰勞及聯絡情感的活動。
註七:「循著祖先的路,直到永遠」。
註八:Taparo,獨立的小山頭。
註九:Radiw,歌或是歌聲。
如果要談論殖民的問題,或許可以從上一代作家經常談的殖民傷痛闡述出發,再經過去除殖民的過程,思考要如何拉開一個與上一代作家不同的距離,我們發現,必須讀更多的書(資料分析)、認識部落(田野調查)或是傾聽長輩的故事,理解族群在歷史上遷徙的流動,找到族群移動的距離與路線,不再只是從「鄉村到都市」、「都市到部落」的線性迴路上去思考原住民族在歷史移動的方向,會開展更多面向,從被殖民往去殖民前進,從被定義的狀態朝向自己定義自己,自己理解自己族群,不在是資訊化、數據化下被認識的原住民。
無人聚會所
雙眼臨淵探出枝枒
在碎裂的磚石上翻找生息
迷路廢棄物
戴上眼鏡
自墟址走向俗世
裊裊升起調查者的帳幕
山無語的隆起背嶺
一塊塊藍鐵皮包圍苔蘚安寧在此聳佇的廢置路燈
野火有時顫抖著迎過風
阻擋蜂巡的航線
山告訴你敵人要來了
騎著馬匹來報信
一則文字進入林間的笑語
石的諾言
讓開成為路
未知的鏡模糊著距離
切割林中老幹的眼睛
廢墟裡的新枝預告死寂
二重身般的歷史身形擺換
銳利走向平行
眼睛重新戴上我
沒有屋頂的廢棄公廁
更加公共的在山中拘留
陷阱內如野狗驚醒的敵人
自行在頸上繫好韁繩
像隻孤鬼貼著矮牆
躲閃凝睇
陶者
空間容納時節
宇宙運動轉變
可以你為核心
我失落的一坏土
使面龐抹消
內裏作為陰冷的居所
凝入血脈、身軀
細痕裏的時間隨風膨脹
以你身為原型塑成貧瘠
呼告彼此破碎的肉身
且行且泣
陽光從裂隙溢入擴張的世界
我得意在漸灼時同時忘卻
窯間你我攏縮同一片漆黑
猶如火山口墜入
深谷愈發燦燃
不敲、不鑄,不試探
亦不如臻秀的瓷般輕吟
高蹈的火星中。我沉音粗礪
髣髴頑石星隕乾癟堅凝
親捧一碗水、一盆花材
薄壁中一片豐滿綠地
冷靜得幽柔脆弱
嘗試吐露大地中的記憶
記得水的流利
記得味覺亦沒有身體
混沌意識時時刻刻檢驗
性質被演化在櫥窗高閣形漸凋敝
時刻臨摹他者的雛型
依稀記得屈辱的形狀
火要像火燃燒時有火星灰飛不滅
我要像我有雙明辨你的手時
我無懼成灰
路過神山
還要翻過多少山頭
一條淺淺的路才撥開野莽探頭
他的雨已失蹤人口
我不知他烏雲的去向
畢竟人有人的方向
魂有魂的落魄
潦倒什麼沒有料到的人
(料到什麼沒有潦倒的人)
若時間有節拍韻奏
我想當一只休止符
在土石降落鄉野前的一瞬
越前,休止於文明還沒進入的時刻
休止於山稜仍在聳立巍巍的深閣
休止於郊荒地帶你我
誰也不見誰以後的民族主義讓讓讓讓吧
讓一張風景照片輕輕帶走
或者想祢是個羞於制止的靜物
路過以後,喪志,拋棄玩物
早起才在幾個山頭翻過獵獵的風
別閱讀方誌、測量部落
往高處走
體溫失調的問題很多
幾個年輕被山脊緊抱時
祢坦露破口
見深深的路一條條痕印
頃刻,敗壞,山河洩漏
那蠻風野雨襲來
一綹稻穗如何安靜
別問我
關世音
1.
若三世有不知人疾貧苦
願坐為一尊關世音菩薩
於層層的門府中參道
究竟涅槃
願化作一屠夫、野人、怨婦
清早五、六時分時時刻刻守候門堂
舉起泣血的標語與生存工具,坐或站
遍佈在人行道與路口
乞討您稀薄的道德與神權
大覺者精煉的法語
或者躺平作為您修煉的苦路
你將踩過我們苦難的身軀
為我們示現高EQ的傳授
何妨左與右臉
此身皆允肯仇敵凌虐
並以警員的防暴帽遮掩
你儘管面露苦愁在拒馬的另一邊
是一面高牆的另一處佛國
心無罣礙某市長的不丹、尼泊爾
2.
你腥無雜念、無奸不摧
此生作為一名幼稚園教師
為未來的未來而努力
轉身之後深怕無電而選擇以核為貴
你深怕膝下有子
且子真將進入千世萬載的近未來
在家出家,對千萬個黑鏡常唸阿彌陀螺
化身千千萬萬個你
你千千萬萬個眼耳鼻舌身意化身的帳號
為人生祈福無災無恙
無所良心不安
你辛勤社會
作為善感的計程車司機
為乘客傾聽每日哀怨
最後一班乘客到家後
故事跳錶一次成為一則笑話
你以地獄為家自乘客的話語中四海流蕩
啤酒、菸絲、泡麵配著社群網站
將陌生人的枉事用以開釋寂寥網民
作為最效率的佈道
匹配趕車時最高檔的技速
示現如何自底層哀極生樂
工作時常愁著沒有故事
下班後將吵雜的收音機關閉
今日逝今日避
今日依然沒有衝進總統府
或者以白米埋製炸彈
3.
某時半刻你曾作為無可為之
偶見社會新聞的大學生
思索轉世喇嘛如何授封的疑問
赤土的西方極樂世界早已研究成果
5G何比天眼他心通
當知是人不撈一民二民三四五民所攢善財
已撈無量千萬民所攢諸善財
披上進口最高級材質袈裟
佛將浴於機戰
捻火蓮開
人人防疫皆於火宅中就近孽槃
現世無道
心懷一位慈母的心思
家事閒餘真羞實煉
坐於蒲團恆常持念
每夜睡前呢喃:「常唸阿彌陀螺,
常唸家家關世音菩薩。」
你是一尊降世久佇人間的菩薩
你是每一位修己不顧人間的
關閉世間聲音的菩薩
to'or──一綹稻穗如何安靜
看著你席地而坐
唸誦瀕危的詩歌
幾滴陳釀的悲傷挪動天空
點亮Mata
長出另一顆心
在剝落四散的土地中
尋索流失的裔名
搭乘潮濕盆地中流離的列車
誰的城市尚未設置祖靈優先車廂
語言穿過彼此交匯出新的信仰
猜想一座山生長痛的緩慢,即使並非巫覡
引釃除魅、疏辭卜筮,預知時光的下落
有誰沉思過庇護的意義!
誰曾扮演巫覡,點燃篝火
燃起記憶
無的箭矢飛向島嶼邊緣的暗流
聲音倏忽熄滅
拒馬袒護謬狂的焰火,眾聲斥駁海潮起落
文明萬化島嶼
幻術擊碎一首首時間無用的懺情
二十多歲上下年代的青年群像
如一列山脈靜默的半島生來默睹蜉蝣
之命,一九九三年陳抗者心內的內核消逝
時間掌握了革命
像座硬冷的工廠
擺疊標註每個謊言年份的罐頭
疾風、驟雨,凱道上不安全的漂島
與路樹之間,逼視你對空張弓
所學語言撰寫陌生的文字
你的板塊飄離太久
遺忘如何以較長時間下來看
一綹稻穗如何安靜
註一:to'or。阿美族語,跟隨之意。
註二:Mata。阿美族語,指眼睛。